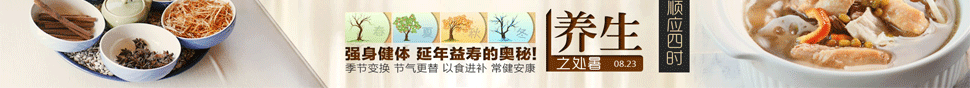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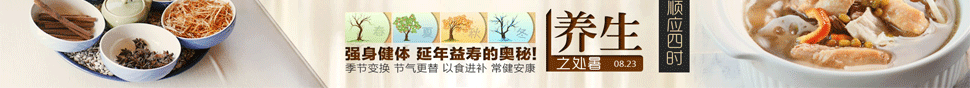
点击上方蓝字 名:《血竭·没药》
作 者:王常婷
出版单位: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11月
作者
简介
王常婷,福建省作协会员。年后开始业余写作。曾获福建省第32届优秀文学作品提名奖;年、年度《泉州文学》优秀作品奖;多组中药题材作品刊发于《福建文学》新实力和聚光灯等专栏;中药诗歌《本草中国情》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并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载。
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忘了喊痛》。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50万余字(行),发表(转载)于《散文》《诗刊》《文艺报》《工人日报》《散文百家》《福建文学》《厦门文学》《泉州文学》等报刊。
内容
简介
医药许家有一秘不外宣的血友病,靠自制的血竭没药散控制病情。几十年后,这一遗传病相继出现在许家的第三代身上。而叶家的第三代远志也有同样的病症。这两家还有一直帮衬着他们的三叔公家,几代人间有着怎样的纠葛恩怨呢?
下南洋的林义生、叶冬花惨死于印尼排华,细莘带着远志和血竭没药秘方逃回国内。细莘从远志的血友病发现家族的秘密。香橼察觉细莘与丈夫的私情,两人在树林争吵时,细莘饮弹而死。正巧,远志和同伴在河对岸用同号子弹的猎枪打鸟。凶手到底是谁?
已经出国的远志面对夜色美酒,闻到的却是当归熟地的香味……
本书以药名入回目,同时也是主人公的姓名,植物的药性与人物的性格纠结,个人的命运与家国变迁穿插在一起,说的是中药故事,更是人生。
前
言
(节选)
别样悲欢逐逝波
——读王常婷《血竭·没药》漫记
曾镇南
一
在读《血竭·没药》这部长篇小说之前,我已被王常婷近些年来陆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吸引;有些作品,甚至让我感到惊艳和震动。她的小说所写出的东南沿海厦、漳、泉一带的乡情土风、方言韵调,以及生活在闽南这一带的平民百姓的打拼、苦做,不惮于迁徙,更敏于趋新求变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特征,正是我这个本地人——虽然我已经“离乡不离腔”在北方城市生活50多年了——所曾经熟悉并感到亲切的,尽管现在有些也感到陌生,甚至骇异了。特别是当她犀利地写出那些南方女性人物辛劳、放达、灵醒、柔韧的生活外观下,有的竟潜伏、纠缠着灵与肉的隐痛、钝痛乃至剧痛的时候,我不免也会为人的生命深处的那种彻骨的悲剧性的痛而感到微微的战栗。还有,她那“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带着天籁之音的文学语言;率真到不觉有些随性、浑然到无意识的逸出畛畦的笔致,更是让我觉得受到一种艺术力的闪击而心折,却又一时感到惘然、怃然而只能止于无言的。
在当代小说作者的繁林中,在层层涌动的诗文作品的星海里,王常婷和她的一系列作品,虽然只是闪烁在遥远的闽南海滨的一小簇微光,而且游离于当代文坛的各种时潮和风调之外;但只要你偶遇之投以一瞥,一定就能够把她清晰地、准确地辨识出来:“哦,这就是那个王常婷”——她的小说的某些地方总是能触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人们灵魂深处小小的不安。在她的作品面前,你不太可能平静地掩卷离去,也很难无动于衷,总会多多少少有点内心的纠结与萦回。这也是我开始读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血竭·没药》就充满了期待和信任的因由。
二
《血竭·没药》写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貌和人生况味呢?这是初读小说的读者大概都会感到有些困惑、迷茫的。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生活的场景,一开始是南洋,印尼的打腊;中间一大段是在福建闽南的乐溪东门兜和华侨新村;最后的尾声则甩出去很长很远,是移居美国已过中年的远志的一个寂寞而怅惘的酒吧酣醉之夜。看起来好像有些分散,但作者散得开,却又收得拢,她用闽南人生活的熏气和家族的血脉把全书的人物和环境归拢到了一起。这是有特定时空的活的闽南人的生命体。它是在闽南之南的一小块乡土上,吸纳了邻省潮汕文化,远揖了遥远的南洋文化,浑融蕴涵而成的一种强韧而善生善变的文化。在小说里,它具象地衍变成一群纸上的生灵转徙歌呼其间的沿海城乡杂居地。在这特定的具体空间里,展开的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段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
《血竭·没药》写的正是这一段既赓续着古早的传统又迎受着社会变动的新机之老闽南人的生活。这闽南之南,海滨一角的独特生活形态被这样平易本真活力四射地写了出来,在我浏览所及的小说中,似乎还是第一次遇见。小说如数家珍般细细写到的吃食、器物、鸡犬、神祇,里巷伦理、旧厝土风,无不让我感到亲切有味,件件牵动着乡情的丝缕。小说形象地显现的祖居东门兜的一个家族生聚繁息出来的许、叶、林三家几代人浮沉起伏的命运、遭际,更是触发了我对家乡父老兄弟、姐丈姑舅们的牵挂和联想。这些又像亲人又似邻人的人物形象,虽然不是用从头到尾、顺序而下的精描细绘的工笔画出的,但作者健笔点到,按压注墨,晕染透纸,人物也就面目神情宛在眼前了。这些时隐时显、载浮载沉的闽南人,或闯荡生死场,爱拼会做,即使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也存一份追求美好生活、护家惜身的本心;或躬逢大世变,跨洋越海,归国离乡各有命,都能顺变平情,于散淡洒脱之中,透出一种对于生的执着与安详。他们之现身作者笔下的尘世,或不见首,或隐其尾,但只需中间有一肢一节,腾挪闪现,便是一条活泼泼真心见性的生命!这些被作者用艺术的熏气吹活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闽南人形象,就如永不定格的云头,变幻为一幅氤氲着弥散着淡淡的中草药味,又混合着茶香、酒气、禅韵的世俗生活与平易人生的浮世绘了。
美文
节选
“血竭,中医常用的药材,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及树干中的树脂。主治跌打肿痛、内伤瘀痛、外伤出血不止、臁疮溃久不合等等,被誉为活血圣药。
没药,中药名,植物的树胶脂,黄色至红棕色,芳香,用于牙膏、香料和药物,其性平、味苦,功能活血行瘀、止痛、生肌。
”一当归
1
南洋的夜,总是有点燥热。
“我没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么生猛吗?”
在心满意足之余,叶冬花有时会犯浑,说一些煞风景的话。趴在她身上还喘着粗气的林义生身子一软,叹了口气,翻到一边,沉沉地睡着了。叶冬花在黑暗中偷笑着,也翻过身,抱住自家男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是遥远故乡的那片海和沙滩,她穿着宽大的短裤踩着潮水捡赤嘴,软软的沙滩把她深深地陷进去,沙子在她脚底下快速地流走了,掏空了,潮水还有流沙带着她,很快就要坠入深不可测的海底黑洞了。她着急地往上提,张开的双臂在空中飞舞,却使不出劲来,发起狠来,大吼一声:“干你佬……”
说粗话对于叶冬花,是下稀饭的咸菜豆豉,如果话里不带点脏话,就觉得生活寡淡无味。来到印尼,她不得不收敛了,因为丈夫林义生骨子里还有点文人习气,还是喜欢女人温文尔雅。在老家,大家都一样大声说话、大口吃饭,他觉得叶冬花的大大咧咧也粗野得活色生香的;可是来印尼,在华人圈子里,女人说粗话还是会让人瞧不起的。叶冬花不想让丈夫为难,能来印尼,她已经很满足了。比起其他同乡,在外拼了一二十年,老婆孩子还是放在家里,林义生只是当个随堂医生,尽管没赚多少钱,能在立稳脚跟后,就把老婆女儿接来印尼,叶冬花已经不知多少次烧香谢菩萨了。
一个人在老家带孩子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下田种地,对叶冬花不算什么,她最怕的是孩子生病时的那种无助。偏偏女儿一点也不像海边的孩子草芥好养,三天两头就发烧,一发烧就得好几天。村里的先生嬷(闽南民间对女性老中医的称呼)一看到叶冬花又抱孩子过来,就摇头:这查姆(闽南话,女人)是皇娘身、乞丐命!每当孩子发病时,冬花看着那烧得不省人事的小不点,感觉天下人都要抛她而去。母亲早年就去世了;父兄讨海,船翻了,人也没了。不安分的丈夫又和人去南洋,除了偶尔的信和薄薄的汇款单,她都快忘了丈夫这回事了。只有这孩子,是她唯一的依赖。幸运的是,女儿虽是大病小病不断,病好了,除了脸色苍白点,也没落下什么病根。
后来当医生的林义生分析:这孩子就是先天体弱,又营养不足,只要一点点风寒、体热,她就受影响;不过这样也好,小病不断,大病不来。也真是的,到了印尼,这孩子读了寄宿学校,不愁吃穿,竟就真的没病没灾的,还出落得高挑漂亮了。
苦苦熬了四五年,丈夫就让同乡带她母女来了。虽然来到的是打腊乡下,但冬花已经很满足了,反正原来住的也是乡下,乡下有乡下的好,可以种菜养鸡鸭。义生说,在乡下,他做随堂医生虽然收入会少了点,可是别的花销会省一些。而且在大城市里,林义生很明白就凭自己的三脚猫功夫,也就看个普通病而已。印尼的随堂医生虽然坐在药店里,但和药店是没关系的,收入是看病的人付的。城里店大欺医,病人虽也多,却不好糊弄,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而打腊这家药房刚好是老乡阿勇开的,阿勇的老婆是达雅人,不仅是附近村民,就是住在深山里的达雅人有病也喜欢到阿勇药房看病取药。
尽管自己很省,林义生却掏出所有积蓄,把刚到印尼的女儿送到了雅加达的华人寄宿学校。他很担心,女儿如果也是住在打腊的话,就会和那些达雅女人一样,围着长长的筒裙,袒着胸,赤着脚,捕鱼,割橡胶。他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自己再苦再累也忍受得了,却不允许下一代受自己的苦。
来了印尼的冬花很快就和当地女人一样赤着脚,穿着筒裙,因为凉快啊;当然没有袒着胸,况且现在袒胸的达雅人也不多了。冬花也跟着学会了割橡胶,虽然林义生的收入要养活她和女儿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个手脚好好的人怎么可以不劳动呢?多挣一点是一点啊。
也因为和大家一起劳动,村里人很快就和她熟了,看她和林医生、阿勇老板都讲闽南话,就好奇地问她闽南话见面打招呼怎么说。冬花一本正经地说:“干你佬!”没错啊,在老家,乡里乡亲见面都是先骂一声,不骂就不亲热了。于是,好玩的人们碰到林医生,大老远就喊:“干你佬!”林义生哭笑不得,眼睁睁看着女人一脸无辜地把“国骂”播撒到异国他乡。
白天,冬花和村民们一起到山上割橡胶;晚上回来,也和大家一样,把家里的地板冲洗得一尘不染。这是冬花觉得南洋人比老家文明的地方,就是无比地爱干净。在印尼待了十来年的丈夫已经习惯了这种讲究,冬花也只能适应。尽管她信奉的还是老一辈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唵喳(肮脏)呷(吃)唵喳大”,一旦做习惯了,也觉得要干干净净才清爽。其实;她从来就是一个没原则的女人。毕竟这里的天气太热了,不清洗的话,屋里就更闷热了。除了地板,冬花每天必擦的还有那张从老家带来的篾席。睡了十几年的篾席,已经都变成暗棕色,光滑油亮,却愈发冰凉。林义生吃过饭,就爱躺在那上面,看书或者发呆。当然如果冬花也方便的话,最好是做做夫妻间的功课。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燥热天气,还是熬了多年单身饥渴的男人变本加厉,林义生在夫妻生活上始终兴致勃勃。守了多年活寡的冬花好不喜欢。偶尔她也会嘴贱,也半真半假追问男人这几年难道就没跟别的女人?其实答案并不是很重要,只要现如今躺在身边的男人是属于自己的就够了。
她很不满的是自己。尽管这对老夫老妻像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可她这块荒废许久的地,却好像就此抛了荒,春风来了,春雨来了,种子播下了一茬又一茬,却都没能生根发芽。一开始林医生还会探讨下关于阴阳交合的道理,按老家习惯,配了好几味药来滋阴养肾,当然最常用的还是老家里常用的四物汤。
四物也是用最普通的当归、熟地、白芍、川芎。煎过的中药渣就顺手倒在门口路上,过往的行人踩过踏过了,那病气也跟着就带走、散开了,据说那样病根才会断绝。以至于有一阵子他家屋里屋外总是一股浓浓的当归熟地味儿。可是药汤喝了,药渣也被人踩到没影了,播下的种子却始终安安静静。到后来,他也绝望了,不为播种,干活却成了他的习惯。篾席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是愈发的油光发亮,可那架木头床却架不住如此折腾,吱吱呀呀,让冬花总担心它有一天就会散架罢工。但在兴头上的男人却是管不了那么多,也只能是女人在事后想起,才拿起铁锤铁钉敲敲打打……
月亮升起来了,月影洒在岛国的椰林橡胶林,也洒在不远处的热带原始森林,达雅人长廊屋檐下的柴刀与头颅闪着阴森森的光。男人女人都睡着了,女人还在做着故乡的梦。梦里,海边的木麻黄在海风里呼啸着,几个男孩女孩在石头巷子里唱着:
“月娘月光光啊……”
2
天蒙蒙亮,热带雨林蒸腾的雾气和太平洋吹来的咸湿的海风氤氲着。冬花戴着斗笠从山上割完橡胶回来,浑身湿漉漉,也不知是汗,还是水雾。
每隔两三天,冬花就得到橡胶园里割一趟橡胶。割橡胶要赶早,晚了太阳出来了,橡胶就干了。在老家讨海也得趁潮汐赶早和晚。冬花习惯了早起,也喜欢早起,感觉做完工作一天还满满的,那都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还可以做多少活啊。
进屋来,走前烧了两把火的一锅地瓜粥,趁着余炭已经烂熟。以前老家渔村土地少、粮食少,所以米饭里总得加些地瓜充饥,常常是一大锅地瓜签(地瓜刨成丝晒干)里没几粒米,吃得人胃里发酸。现在米够吃了,那粥没加点地瓜反倒是就没味道了。冬花从瓦罐里掏出了一把咸菜,下点油炒了下,加上咸咸的豆豉,早餐算是解决了。在吃上,林义生很容易满足,经历过忍饥挨饿的年月,能吃饱,偶尔还能换换花样,这样的日子在当年是怎么也不敢想象的。
如果是不割胶的早上,冬花会去海边滩涂捡些小鱼虾回来,就着酱油水一炣,加上姜蒜,新鲜咸香,林义生就好这口。让冬花不能理解的是,当地人也不富裕,可他们都不屑于吃这种小鱼,因为鱼刺太多,宁可花钱买渔船上捕捞的没什么刺的大鱼。没刺的鱼那还能算鱼吗?冬花和林义生都来自海边,从老一辈传下来的就是多刺的鱼才鲜甜。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些是不要钱的,只要你肯起早或贪黑,趁着潮水退去时,去搜寻捡拾那就是你的。多好!晚了,海水涨潮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即使还没涨潮,太阳一出来,赤道海岛的烈日下,搁浅的鱼虾个把小时就发臭了。冬花早就算好了这个地方涨潮的规律,所以每次去都不会空手,有时捡得多了,还可以腌咸鱼。只是因为这里天气炎热,腌东西并不好把握,不仅盐要下得多,晒干也成问题,常常还是艳阳高照,刚把东西拿出去晒,老天忽然就下起大雨。为了保险,那就放屋里阴干吧,可是在热带海岛潮湿的空气里,一不小心鱼很快就发霉烂掉了。就这样在与太阳阵雨赛跑的日子里,冬花还是腌出了一笸箩一笸箩的咸鱼,还有豆豉。
在闽南渔村,豆豉是家常必备的。出海打鱼,十天半月,带的除了柴米油盐就是豆豉了。从小吃到大,不觉得好吃,可真到了他乡,没这东西,吃饭竟就没味道了。肠胃是有记忆的。还好,南洋的炎热天气很适合煮好的豆子发酵,冬花只要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xianglongxueshu.com/xlxszp/4928.html


